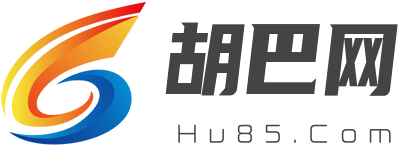□张一芳
记得一副热食担子,在老家渔乡的这里那里歇着,或海边滩头、晒场边上;或庙所戏场、街坊拐角。那时我在海边过生活,它在我的记忆中,是随时都能跳显出来的那一种,并且始终如一地有如它的用场的专一性,就只是卖粽子。

担子是木制的四方柜的样子,有挑梁,是两只。一只放着圆筒型的洋铁皮烧锅,底下的红泥小炉,烧着微微的炭火;另一只则可算是储藏柜,上一格存放煮过的粽子,下一格放着竹筷和一摞青花小碟子。买主来了,卖粽人麻利地取出一个或两个,不紧不慢地解开缚绳,揭去竹箬,青花碟里是一个或者两个嫩糯糯、香腾腾温而不烫好看又好吃的粽团子。
我那时候的吃粽样子和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在担子边上一蹲,头上一片暖阳罩着,耳畔或许会有三两声鸥鸣掉落,这时候扒拉开粽团,夹一小筷在嘴里抿着,那个情调那个散淡,不是在堂屋的长条板凳上正儿八经坐着感觉的来。我于是猜想卖粽人也一定是渔家出身,一是会按时令节次轮番变换着把鱼肚、馒鲞、鱿鱼干、虾米、蛏子肉等干鲜海产当作料,与栗子、花生、香菇之类山珍搭配,相互得味,揣摩渔民的心思和口感所获的智慧。二是最会做“海头人”的生意,在渔埠头歇担揽客,给从风浪里回来的人递上一碟温馨,回家的感觉就有了。我就不只把吃粽当吃粽,那时吃的就是那份感觉,无论是出海候潮或是归埠上岸,遇着担子正歇着,买一个先填了肚子,一边看着周遭男女人来人往,吆喝笑骂或者吹牛喷天。有时归港已是夜深,浪花和汗渍满身,见着油纸灯笼下的卖粽担子,就和见着亲人一样!
在家乡渔村,粽子就被演绎成了四时常食,不惟端午才有。
其实,一个粽子的品质蕴涵,是那一块卤肉的香味。肉要选得肥瘦恰当,卤得也要适时足料,主料糯米和所有作料都加入到提味的队伍,甚至包括外裹的竹箬和系缚的棕榈叶。
煮成后是鲜嫩带油,香味诱人,既能渗入到粽子的角角落落,又能在周边远近萦萦散发,这粽子便只被叫作“肉粽”了。但这“肉”字,是绝对不能读作字面音的,否则就外行了。要读成“墨”和“押”的合成音。好端端一个“肉”字被读成这样,实在是秉承了闽南方言的精髓,如把“锅”说是“鼎”,把“粥”说是“糜”,都是闽南祖先的智慧,保留着原乡的口语传承,其实又是很草根很底层很老百姓的。有人把它读作“妈”“麻”的普通话字音,实在是不懂民俗不懂根源使然。
还记得当时比较出名的卖粽人,有同是渔人出身的“青盲连宝”和“蒯手乌甜”,都是海里辛苦劳碌上得岸来的。一个是视力减弱,一个是手有伤残,改行又改业。并且和我一样都是渔乡通行的栲衣和拢裤的穿着,却不改装扮。又各有自己的手艺和本领,甚至连糯米的浸制方法也各有讲究。再后来则有徐老三。徐老三年长歇业后,就再没有挑担卖粽这道风景了。
其实,粽子裹着的是我们渔乡的古早味,是留在记忆中的过去时。前些日子回乡找感觉,倒是找到有卖粽子的,都是店铺的摆设,其中有一片是玻璃门面的蛋糕饼食店捎带卖粽子,并且是一个修眉画眼口红抹得像西山夕阳的女孩在张罗。
我走进小店,蓦然有所感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虽非怀旧却有着怀旧意味的淡然,淡然之中亦有几分亲切。也就想,若有一位相熟的朋友,无论世事变化,时光流逝,依然故我地保持了一份乡情和乡思,该多好啊!我就想,世道总是这样变化的,大约是到了要变化的时节了吧。搞不懂的是怎么有些人和事,三晃两晃,就都变了呢?
于是就只是希望这家小店能够长久地卖着粽子,以便给我一些关于乡思的提示。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本文来自一场戏投稿,不代表胡巴网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hu85.com/320293.html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xxxxx@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