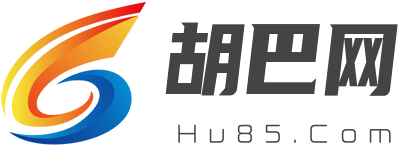塞什·吉尔博/著、 秦兆凯/译
译者序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格林伯格和罗森伯格等的艺术批评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美国现代绘画的国际地位,埃尔文·桑德勒(Irving Sandler)的专著《美国绘画的胜利》(1970年)则更进一步将这一现象叙述并沉淀为历史。于是,在人们心里慢慢形成一种印象:似乎抽象表现主义的成功就纯粹是由于美国绘画的卓越。1983年出版的法国人塞什·吉尔博撰写的《纽约如何窃取了现代艺术的观念:抽象表现主义、自由和冷战》则对这种美国现代绘画的胜利提出了质疑。
吉尔博的中心论点是:“美国前卫在国内以及国际上史无前例的成功,并非如欧洲和美国评论家通常所说的那样,仅仅由于审美和风格的因素,并且还是,甚至更是由于这一运动的意识形态共鸣。”吉尔博希望通过还原这场运动的社会、政治背景来“揭示战后抽象表现主义艺术所取得的主导地位仅仅是由于形式上优势的习惯看法的无知”。在吉尔博看来,由于缺少对这一时期产生的形象和文本背后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分析,这种新的美国艺术的支配地位常常被视为不可避免的事实,甚至是一个神圣的法令;而其中的原因从未被分析过。他认为,抽象表现主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作品和支持它的思想观念“与1948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开始主导美国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相对紧密地保持了一致”。由于前卫艺术自我标榜的中立,它很快就被政府机构和私人组织征募到反对苏维埃文化扩张的斗争中。这暗示了抽象表现主义在冷战期间被作为宣传工具所利用的背后原因。
与此前对抽象表现主义研究注重形式、媒介、风格、审美因素不同,吉尔博将艺术家的作品和批评家的辩护置于冷战时期的社会政治语境之中来解读,探寻这些因素背后的社会政治原因。从方法论角度讲,吉尔博的社会艺术史代表了70年代以来逐渐盛行的被统称为新艺术史的趋势。其目的,用作者自己的话讲,在于对抽象表现主义的历史进行重估。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艺术界目睹了一个美国前卫艺术运动的诞生与发展,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它就成功地将西方文化中心从巴黎转移至纽约。本书的目的就是调研这一成为前卫主导风格的抽象表现主义的历史和重要意义。
至今,大多数关于这一时期艺术的研究专注于行动美学(马吉特·洛威尔、哈罗德·罗森伯格)或是作品的形式品质,即媒介和风格的影响(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威廉·鲁宾、迈克尔·佛莱德、埃尔文·桑德勒)。相比之下,我试图剖析这一时期的政治和文化给予我们的暗示。我的中心论点是,美国前卫在国内以及国际上史无前例的成功,并非如欧洲和美国评论家通常所说的那样,仅仅由于审美和风格的因素,〔1〕并且还是,甚至更是由于这一运动的意识形态共鸣。
本书是关于抽象表现主义的社会研究,它试图搞清美国前卫艺术因何采取抽象的形式以及这种形式如此奏效的原因。这些问题的答案是错综复杂的,然而我相信,一旦有关画家的作品及写作被置于与历史和经济背景的关系之中,这些答案就会清晰地显现出来。通过还原这场运动的语境,该研究将揭示战后抽象表现主义艺术所取得的主导地位仅仅是由于形式上优势的习惯看法的无知。
在有助于塑造抽象表现主义和确保其成功的一系列因素中,最显著的当属去马克思主义化的缓慢过程,还有自1939年以来纽约某些左翼反斯大林群体的去政治化,后者伴随着战时民族主义情绪的迅速上升。此后,由于冷战的加剧以及马歇尔计划最终获得了国会的批准,一个富有和强大的中产阶级强化了它的立场:这些情况也将在我们的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
通过将第一手资料以及众所周知的批评文献置于冷战历史的语境中,我希望阐明驱使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精心炮制出一种折中风格的动机。这一造型风格,在与欧洲传统保持对话的同时,为响应二战后崛起的崭新的美国文化需求,塑造了一个美国艺术的本土形象。
我试图重现这样一个缓慢的过程:随着一种新的图像生产方式的产生,这个崭露头角的前卫于1947年和1948年间详细阐述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尽管最初有不确定性,这种意识形态与风格的结合迅速稳固下来。虽然同样来自左翼的反斯大林主义,它们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第三种方式,”抽象的和表现主义的,据说它可以避免“左”的和右的极端,或如当时所说的,既是被解放的又是解放性的。
这种新的形式确实与现代主义传统产生了某种对话,但除此之外,它似乎还为前卫艺术家提供了一种在避免宣传和图解艺术的同时保持其社会责任感的途径(社会责任感对于大萧条一代的艺术家是如此重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政治的非政治主义。本书即是要引起人们对这一遮蔽游戏的关注。
我无意将任何确切的政治动机转嫁到前卫艺术家头上,或者暗示他们的行为是某种阴谋的产物。我的论点是:经过一次次的妥协、拒绝,以及调整,源于左翼内部挫折的艺术家的反叛,渐渐地改变了它的意义,直到最终成为主流价值的代表,只不过以一种唯有少数人可以理解(延续着现代主义传统)的方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前卫的思想观念被人为地与体现于阿瑟·施莱辛格《生命攸关的中间地带》一书中的正在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保持着一致(尽管这种改变对于所涉及的艺术家来说不是没有问题的)。
这自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然而在此我所要做的是,重新审视一个常常被与其产生的历史环境隔离开来研究的艺术运动和风格。我给自己制定的任务并不简单,如果仅仅是由于在美国的文化史上首次有一个影响深远的前卫运动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功——鉴于始终阻止现代主义在美国文化界立足的种种困难,这种成功尤其惊人。〔2〕
在我看来,以下因素均为纽约前卫“现象”的本质:前卫的目的、功能、意识形态以及成就。这里提出的另一重要并且同样复杂的问题是:为何那么多的画家从30年代现实主义的宣传性绘画(不管是革命的、自由主义的,还是反动的灵感来源)转变到后来坚定的前卫式绘画?〔3〕
前卫艺术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作品和支持它的思想观念——由艺术家的文字所表达以及图像所传达的——与1948年总统选举之后开始主导美国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相对紧密地保持了一致。这是一种由史莱辛格在他的《生命攸关的中间地带》中阐明的“新自由主义”,一种既不同于保守的右翼,又不同于共产主义左翼的意识形态。它不仅为前卫的异议留出空间,而且给予这种异议以最重要的地位。
为了避免误解,有必要明确指出,这个前卫的胜利既不是全面的也非普遍的,而是一个典型的前卫式的,即脆弱和不明确的胜利,因为它不断遭到来自艺术界中对立趋势的威胁。因此,当美国进入令人窒息的麦卡锡主义时期之后,有争议的前卫艺术变成了更加宝贵的商品。
尽管在当时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如果说抽象表现主义早在1948年就取得了胜利,这句话一点都不自相矛盾。这些攻击有来自左翼的,有来自右翼的,还有民粹主义的,甚至来自杜鲁门总统本人的。这就是真正的历史矛盾的力量发生作用的地方。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杜鲁门对现代艺术的反应如同一个“最后的堂代罗”(乔治·堂代罗是因“现代艺术等同于共产主义”的等式闻名的来自密西根的臭名昭著的参议员),但是在他的任期内,美国情报机构与现代艺术博物馆早在1947年就已经开始推行前卫艺术。
这种分歧说明文化被政治化并且在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中的重要程度,正如杜鲁门总统在1948年3月17日的广播讲话中所暗示的:“我们一定不要被世界目前面临的问题所迷惑——即专制与自由的对抗……更糟糕的是,共产主义否定上帝的存在。”〔4〕同年4月4日,这位总统在日记中记录了对现代艺术非直接的而积极的评价,他坚信艺术并非无辜,在这个紧张的心理战时期,艺术中渗透着政治。然而对于他来说,美国作为一个文化领袖的新形象毫无意义,尽管这对于他的政府中的某些官员来说如此重要:
早上10点钟去散步。到了梅龙美术馆并且成功说服值班看管让我进去。看了从德国盐矿发现的传统大师作品,一些出自荷尔拜因、哈尔斯、鲁本斯、伦勃朗以及其他人之手的名作。看着那些完美的作品真是一种享受,然后想到了懒惰而古怪的现代派。这就像将基督与列宁相比。但愿再来一次觉醒。我们需要以赛亚、施洗者约翰、马丁·路德——但愿他早一点儿到来。〔5〕
波洛克、罗斯科和纽曼不是这位总统要寻找的先知。相反,对他们的认可只能来自现代艺术博物馆。这种矛盾构成了形成这本书的素材的一部分。
如果有必要解释这个前卫为什么并如何征服了美国艺术市场以及窃取了文化领袖的形象,同样重要的是分析这个前卫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并且最重要的是理解这个前卫与巴黎所维持的(经常是不得已的)对抗性关系。
为什么是巴黎呢?因为尽管战争的蹂躏,巴黎的艺术依旧代表着西方文化,并且对于纽约的艺术家来讲是现代主义思想的根源。基于这一原因,我试图在这项研究中自始至终地揭示在纽约与巴黎所发生的一切之间的联系。
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期,巴黎不愿正视影响着欧美经济和艺术关系的巨变。当纽约通过它的发言人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宣布,她最终已经取得国际文化中心的地位并且取代巴黎成为西方世界文化的象征时,法国的首都在经济或政治上都无力反抗。除了漫不经心的不屑之外她什么都不能做。这种自我满足的无所作为,仅仅部分地由于艺术界的极端政治分化,加速了巴黎的没落,并且使巴黎的艺术女神进入睡眠状态,直到60年代被再次唤醒。此时法国的收藏家们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来完成他们的订单。正如皮埃尔·卡巴奈所解释的:
有着罗马大奖、学院、秋季沙龙及艺术修复专家的法国,对退休比对发现更感兴趣,内阁马屁精的法国——整个瘫痪和恐惧的共济会做出了继续停滞不前因循守旧的巴黎画派道路的决定。睡美人现在需要的不是白马王子,而是当头一棒。〔6〕
法国,几乎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切——有人说甚至失去了她的荣誉——开始紧紧抓住几个世纪以来整个世界都认为属于她的东西:文化霸权。因此,美国将艺术创作的中心从巴黎转移至纽约绝不是一件小事。
我的故事止于1951年,这一年纽约的前卫群体组织了所谓的第九街画展,它同时作为前卫成功和衰落的象征(这一运动中最著名的艺术家没有参加)。〔7〕当政治宣传的咆哮声变得震耳欲聋时,纽约信心满满地做好了摧毁巴黎的古老梦想的准备,美国的文化浪潮将要冲击整个欧洲。
为什么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个曾被多次研究的课题呢?部分原因是,美国超级前卫(据说是现代主义链条上的最后一环)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理想主义看法甚至在今天仍然流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和欧洲的最新艺术策略。〔8〕另一部分还因为没有一个关于这一时期的、将艺术与参与审美生产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一起分析的、真正批判性的历史。
读者也许会有这样的印象,由于一些著作致力于纽约画派历史的研究,于是认为这一前卫的历史已经被书写。其实不然。仅仅是抽象表现主义的胜利被得到大肆鼓吹而已。从山姆·亨特的《现代美国绘画和雕塑》(1959年)到芭芭拉·柔斯的《1900年以来的美国艺术》(1967年),再到埃尔文·桑德勒的《美国绘画的胜利》(1970年),我们被给予一个又一个正面而乐观的描述,这些文字使人不禁想起过去在高中所教授的历史:讲述一连串枯燥的胜利与失败的战役。
仿佛为了证实我的指控,埃尔文·桑德勒(Irving Sandler)在他的引言中声明,希望他的著作能体现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关于历史学家的构想:即“历史学家从一个身居其中,一个局内人而不是局外人的视角,如同一个本地人而不是外国人那样,充满同情地写作。”〔9〕不消说,我个人对历史学家的构想正好与这种理想主义的定义相反。所有这些正面的、富有启迪性的关于美国艺术的描述,最终将遮蔽艺术家作品中那些富有生气的、真实以及矛盾的内容。我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试图将“负面的”东西纳入这个故事,就像乔治·杜比所解释的那样:
过去的生命所留下的一部分是他们的话语,不管是以写作的还是造型的形式。我以为,未来最惊人的发现将来自发现这种话语忽略了什么,是自愿地还是不自愿地,从而确定什么被隐藏了,有意还是无意地。
我们所需要的是崭新的学术工具,比我们目前拥有的更适合的工具,以便显示出看到的东西中负面的东西,暴露人们故意掩盖的事物。偶尔,这些会突然偶然地自我显现,但是大多数时候它们必须在所说的字里行间被仔细地解读。〔10〕
由于缺少对这一时期产生的形象和文本背后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分析,这种新的美国艺术的支配地位常常被视为不可避免的事实,甚至是一个神圣的法令;而其中的原因从未被分析过。这种对过去的记叙是由本着要支撑这一观点的明确目的而收集的证据所构建的,其真实性不言自明。这里所强调的是,纽约的艺术对于整个世界的艺术发展至关重要,并且产生于走向纯粹的现代艺术的漫长征途过程中的最新阶段。这样的历史自然支持由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阿尔弗莱德·巴尔(Alfred Barr)所推崇的形式分析,这样的分析也是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所终身捍卫的。〔11〕
有关这一主题最流行与权威的著作是桑德勒的《美国绘画的胜利》。〔12〕这部书从形式角度讨论每位前卫艺术家的作品,将每件作品按照“行动绘画”或“色域绘画”分类。其中的两个章节专门讨论“社会背景”,以及画家们发展的艺术环境。桑德勒在书中没有一次试图对手中掌握的文献、艺术家的观念系统或前卫的功能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同时,他忽略了他所操纵的符号的意识形态内容。他的分析是枯燥并且非历史性的,尤其反映在他对手写文件、访谈以及评论不遵循系统编年顺序的混乱使用,这使他的讨论丧失了一切历史意义。他被简化和分类的欲望所驱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象征系统发生全面崩溃的时候,试图用一个简单的模式替代战后发生在艺术界混乱的辩论,而所有复杂性都避而不谈。如此建构的形象从逻辑和统计学意义上似乎很适当,但是由于它所忽略和遗漏的部分,是不真实的。
这种孤立的描述(特定时期某些纽约艺术家群体的历史)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尽管他的博学,桑德勒仅仅满足于描写事物的视觉表面,而拒绝解释或分析隐藏在背后的谣言、抗议及冲突。后者告诉我们还有不为人知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事情的真正核心所在。然而,尽管桑德勒始终专注于事物的表面,他无意间吐露的几个词却暴露出另一被隐藏的故事和历史,尽管这种历史一直被抑制、排除在执意注重正面形象的叙事之外。丝毫没有被文字的分量所吓倒,像“世界大战”和“冷战”这种有启示作用的词在不经意间偶尔流露出来。
只是这个胜利者的历史缺乏深度,仿佛它是在没有同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发生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展开的。桑德勒的书之所以像宣传,是由于它是单向度的:
艺术史家对待其对象的用力过度往往将自己——尽管在解读作品方面技术上的成熟——变成一个不加鉴别的崇拜者。〔13〕
然而桑德勒在第一章中确实谈到了历史,他简要描述了大萧条时期提出的审美问题。这是一个混乱的时期,其间,政治讨论在艺术家中间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不可能为艺术史家所忽视。但是,桑德勒提到这段时间的历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将30年代与战后的艺术区别开来。对于桑德勒来讲,由于战后艺术避免了从政治问题及意识形态到艺术的直接转化,因而才能够与早期现代艺术在平等的基础上取得国际地位。虽然他承认“政治事件严重地影响了美国艺术在40年代初期的发展”,却并未说这种政治的重要性在哪里。此外,该书的其余部分对前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几乎闭口未谈。
这类艺术史的构成元素并不陌生:详细的年表、奖赏的分配(谁最先做了什么)、影响研究、分类、群体的辩解以及圣徒传。这种历史的碎片化的累积效应是“去描述性的”:这种方式摧毁历史,将其消除,并排除对被战争所撕裂并且正在尽力自我缝合的复杂而脆弱的社会结构理解的可能。
整个的社会结构已经被摧毁,政治生活被自上而下地重新定向,知识生活被击成碎片。战后时期的文化史是一个建立在世界和美国经济变革的崭新基础上重建美国文化的历史。它是对社会价值和文化符号重估的历史。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书写文化史而对渗透其中又被其渗透的、更广泛意义上的历史避而不谈呢?美国艺术的历史,只有当社会不再被分割成孤立的细胞,只有当社会、经济、文化和象征因素之间的调节不被抹杀的情况下,才能得以书写。因而,重要的是不要轻视或忽略这些错误的路径、被遗忘的艺术家、被拒绝的作品,这些将从另一角度说明情况。以如此的方式审视对象并非研究领域的碎片化,而是为了界定它、集中调查、更好地定义和研究对象,因而使其接受更仔细的审视。
此外,还应对近年来另一类著作的出现引起注意,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试图对这一阶段更具批判性的理解的尝试:我是指多尔·阿仕顿、麦克斯·科兹洛夫、伊娃·科克罗夫特、简·德哈特·马修斯、大卫和塞西尔·舍皮偌以及法国的让·劳德的文字。〔14〕因此,我不是第一个或唯一对美国艺术史的所谓“权威”提出批评的学者。事实上,这个权威团体在过去的五年里并不像从前那样活跃,它面临着来自社会学者和历史学家的批判性攻击。后者决意将艺术置于原来的语境中去理解,并且试图重建艺术与政治,特别是抽象艺术与冷战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但是这些声音如同荒野中的呐喊,几乎被令人窒息的关于风格影响的讨论无止尽的杂音所淹没。后者往往出自学生之手,他们不愿意反驳那些由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的朋友、倡导者以及崇拜者(例如格林伯格、罗森伯格、托马斯·海斯和佛兰克·奥哈拉)所写的文字。这是美国现代艺术史的悲剧。早期由批评家写的论战式文字以及艺术家访谈,最初作为前卫战场上射出的子弹,多年来已经获得了坚不可摧的神圣地位。它们被无休止地修改、吸收、结合并加以利用。具有仪式感的重复最终使它们似乎高不可攀。
多尔·阿仕顿(Dore Ashton)的《纽约画派:文化的审判》也未能避免这个陷阱,尽管她赞成艺术家根植于自己环境的看法。可惜她涉及的面太广(探讨了30年代至60年代的艺术、哲学、音乐等)。她掺入很多奇闻异事和各种各样的细节,从文学对某些绘画的影响,谈到假定的一首乐曲对纽约艺术的整体影响。构成40年代文化现实的事实、关系和张力被一连串按主题划分的历史所掩埋。其结果是,编年顺序被打乱,随之丧失的还有研究前卫与其发展环境关系的唯一机会(或如阿仕顿所言,使花卉生长的堆肥)。
仿照麦克斯·科兹洛夫(Max Kozloff)和伊娃·科克罗夫特(Eva Cockroft)的例子,二者分别于1973年和1974年在《艺术论坛》杂志发表了引人注目的关于艺术与政治关系的文章,历史学家简·德哈特·马修斯(Jane de Hart Mathews)考察了美国现代艺术在麦卡锡时代所遭遇的问题。但是,如同两篇她所效仿的文章一样,马修斯探讨了一个艺术与政治紧密相连的时期,这一时期,二者的联系显而易见并且得以公开讨论,因此很难被错过。〔15〕
我们的课题迄今免受批判性审视的情况不仅发生在美国,法国的批评,自6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理解法国文化霸权崩溃的原因,明显对这一阶段美国艺术的历史过于着迷而不能用批判的眼光来分析这种形势。法国的首席美国艺术专家马斯林·普雷奈特(Marcelin Pleynet)用从法国人少有了解的美国作者那里借来的相同的神秘人物装点着他的多部著作。〔16〕
让·劳德(Jean Laude)并非前卫或美国的神圣的盲目信仰者,同样证明未能穿透这种烟幕。尽管他尝试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艺术的事实,他的研究为所依赖的二手资料的意识形态的不透明所阻碍。它仅仅复制了上面所批评的同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劳德陷入了恶性循环。打破这种循环的唯一办法是:愿意进行大量的档案整理工作,并且通过检验前卫形成时期占主导地位以外的艺术思想和写作方式,拓宽辩论的范围。
尽管这些修正习惯看法以及将辩证因素引入这一领域的小心尝试,魔鬼并没有被驱除,正如我们在罗伯特·霍布斯(Robert Hobbs)同盖尔·莱文(Gail Levine)策展的“抽象表现主义:形成时期”可以看到的那样。〔17〕不为他们工作的乏味所吓到,这两位学者把注意力放在同一批人物身上,并且把这个古老的故事又重述了一遍。唯一的不同是,这次他们提供了比他们的前辈甚至更多的关于日期、风格影响、时间顺序的细节。事实上,这些细节的程度和体量达到了噩梦般的尺度。
相对于盖尔·莱文简单化的“研究”,罗伯特·霍布斯试图给予这些艺术家的作品的某个方面以新的认识。但是他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有问题,因为他潜在的想法不是搞明白为何这些艺术家成功了而其他人失败了,而是发掘尽可能多的早期作品以及英雄式的尝试,这么做仅仅强化了占统治地位的神话。〔18〕难道更重要的不是将这些作品与其他当时共享纽约的聚光灯,甚至作品比后来更加成功的画家更好的一起考虑吗?那些像拜伦·布朗斯(Byron Brownes)、卡尔·霍迪斯(Carl Holtys)、卡尔·科纳斯(Karl Knaths)、巴尔克姆·格林斯(Balcomb Greenes)、查尔斯·赛里格(Charles Seligers)的艺术家现在怎样了呢? 抽象表现主义再一次被封藏于一个中性的玻璃罩之内并且免受任何不受欢迎的细菌的传染,以及可能打扰这种可贵的和谐的外来者的入侵。如今已经成为博物馆内的收藏,在这种环境展出的作品都有一个“只看不许碰”的标记。
大致翻阅一下《艺术论坛》上两篇由科兹洛夫和科克罗夫特撰写的文章,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构想这本书的时候我选择这个时间和观念范围。这两篇文章涉及到只有近来才被某些艺术史家发现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从未被掩盖:即抽象表现主义在冷战期间被作为宣传工具所利用的事实。由于前卫艺术自我标榜的中立,它很快就被政府机构和私人组织征募到反对苏维埃文化扩张的斗争中。尽管这一事实在50年代在媒体上公开和在艺术家中间私下讨论过,只有最近才由于科兹洛夫而重新成为焦点,他的文章的价值在于将美国艺术的主导地位放在政治语境中来解读。科兹洛夫提醒我们,艺术史家同样患有拉塞尔·雅各比所说的“社会性失忆”。〔19〕这种失忆部分来自作为对麦卡锡时期创伤的回应而自我强加的审查。〔20〕
我认为,伊娃·科克罗夫特在如下文字中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想要了解为什么一个特定的艺术运动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取得成功,需要检验赞助的细节以及当权者的意识形态需求。〔21〕但是她的研究仅仅涉及了抽象表现主义的成功时期以及50年代的现代艺术博物馆。
从时间顺序讲,我的工作止于科兹洛夫和科克罗夫特开始的地方,但是从观念角度讲,我在他们结束的地方开始。我的注意力集中于夹在直接和公开与政治相联系的两个时期之间的“非政治”年代,即介于大萧条时期的“社会艺术”与50年代利用抽象表现主义作为宣传之间的年代。我希望讲一讲1946年至1951年期间那安静的几年。此外,这种安静只是一种幻觉:人们只要仔细听,它就会成为泡影。
怀着解开艺术与社会关系复杂脉络的希望,我详细研究了多种绘画和相关文本的年代,相信一旦在具体事件的背景上予以审视,它们的意义就不再神秘。我尤其研究了巴奈特·纽曼、马克·罗斯科、阿道夫·戈特利布、杰克逊·波洛克的绘画与写作,以及这一前卫群体在1947年至1948年间放弃再现式绘画的决定。〔22〕 这将有助于搞清楚为什么关于冷战历史的详细知识对于我们理解这个主题如此关键,并且对于分析这一运动的艺术风格有着决定性作用。
我无意重写冷战的历史。这是一个被广为研究和争论的领域,任何冒险进入这一领域的人都有陷入困境的危险。我也不希望卷入何方引起冷战的二元论辩论——在我看来这些争论本身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不过我很想利用其他历史学家的,尤其是所谓修正主义者的研究。尽管他们的某些观点过于简单化,总的来说,他们强调某些政治危机人为的本质,以及这些危机对美国文化和人民的影响程度。由于1946年和1950年间吸引西方世界关注的集体歇斯底里的力量和影响是本书研究的艺术家作品中的中心主题,理解政府采纳的和修正主义者分析的政治策略就变得尤为重要。
我对在美俄之间分摊冷战的责任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公众对美国政府和媒体伪造的苏联威胁的形象是如何反应的。对我来讲,理解这种反应比理解这种危机的现实更为重要。在此我还应补充一点,在我看来,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在美国的工作已经导致对冷战有意义的重新评估,而至今同一时期的艺术史仍然不受这种重估的影响。在艺术领域,阿瑟·施莱辛格乐观的意识形态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么,我的抱负是对于抽象表现主义历史的类似重估做出贡献,同时防止过度简单化的危险。通过向艺术史注入一剂真正的历史,我希望重新恢复这一课题最初的复杂性,而其他历史学者在此方面往往陷入细节的泥潭。因此,对于形式的影响,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它们对于我的课题来讲并不重要,并且已经被其他人充分地谈论过了。相反,我试图重建抽象表现主义与政治间那个常常是困难的对话,即一场贯穿我调查的时期的对话。
虽然我避免主题和传记式的研究,它们往往隔断艺术与历史的联系,我的意图绝不是排除、隔离或忽视艺术家或生产者。在某种程度上我希望通过对艺术市场本质变化的分析,给予纽约画派的艺术一个唯物主义的历史。但我同时紧密关注美国现代艺术家的抱负,以及他们对闯入美国社会各个领域冷战的残酷所做出的回应。
当然,我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我设计的这条路径的不得人心。这同抵制将艺术的理想价值扯入政治和意识形态泥潭的看法有关。我对这种反对不予理睬,因为我确信,尽管这种方法可能一定程度上使艺术的光彩暗淡,这一损失将在现实和真理的获得方面得到超值补偿。艺术创作的过程将得到公开,并且艺术家应付困难的日常现实以及象征性创作问题的情景将再次被展示。在1949年写给马克·罗斯科的一封信中,安德烈·费宁格提到艺术家摆脱日常纷扰时的困难:
难道我们不是在歇斯底里中失去了生活的乐趣——难道一个人要想继续,不是只是需要努力工作吗?〔23〕
此外,当美国的政治气候如同50年代一样极端保守的时候,尝试“修正”很可能不得人心。冷战一直是一个爆炸性的主题:它见证了一系列70年代震撼美国文化的论战。两个来自《纽约时报》的例子将足以说明基于艺术的社会角色的批判性研究有多难,特别是由此立场出发的战后美国艺术研究。〔24〕
在回应《艺术论坛》上一篇卡洛·邓肯(Carol Duncan)批评“革命年代”展览的文章时,〔25〕希尔顿·克莱默,《纽约时报》的艺术批评家,通常较温和的一个作者,以少有的猛烈做出反应:这个问题很重要。邓肯在他的文章中坚持认为,这个展览完全是采用非历史的,因此令人迷惑的方式构想的——对于革命艺术的展览来说尤其令人愤怒:
人们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艺术家主要被艺术史所驱使,并且仅仅寻求模仿过去的艺术。政治和历史仅仅在描绘国王或皇帝那些露骨的宣传性作品中才被提及。〔26〕
克莱默以一篇题为《在“艺术论坛”,糊涂的马克思主义替代了批评》的文章做出回应。他借机攻击《艺术论坛》的编辑政策,并间接批评了麦克斯·科兹洛夫和约翰·科普兰斯,二者在未牺牲与艺术市场联系前提下,试图扩大艺术生产的讨论范围,包括作品产生的社会和政治语境。在称卡洛·邓肯为毛主义者之后,克莱默精确地指出任何当代艺术杂志都要面临的关键问题:
这是对《艺术论坛》想要干什么的一个比较好的概括,很想知道这个杂志的资产阶级广告商——主要是从事被这个杂志视为反人类罪行的生意的艺术商人——将会支持它的新路线多久。〔27〕
一年半以后科兹洛夫与他的合作者们被取而代之,以便将这个杂志转向不那么危险的形式主义。这一切好像就在不久以前。克莱默连同罗伯特·罗森布朗所攻击的是艺术的去中立化,对艺术根源的挖掘及对它隐藏的机制和矛盾的暴露。
从前面所述已经非常明显,如果艺术的去中立化很难,讨论冷战甚至更难。它会唤起可能被认为已经扑灭的激情。第二个例子证实了这一断言。随着好几部涉及这个富于争议的美国政治时期的著作及电影的公开,又是克莱默,利用《纽约时报》(1976年10月)作为论坛,使一个二十多年前用于支持成立众议院反美活动委员会的论点死灰复燃。克莱默试图使那些为“修正主义”历史学家辩解的人士名誉扫地。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该报被大量歇斯底里的观众来信所淹没,那情形使人想起战后类似的大爆发。讨论沉睡在意识深处的禁忌话题似乎是粗俗的,这些有害的话题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过问的。
我的工作瞄准所有这些问题交集的地方。我希望填补这个已经由几名学者注意到的空白。例如,在一本1980年的波洛克素描图录中,伯尼斯·柔斯写道: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美国守旧的背景下,鉴于美国艺术直至1946年和1947年的情况,如何可能取得如此彻底的转变——不仅是美国艺术并且是美国在艺术中的角色;如何能够不仅加入“主流”而且超越它并引发一场艺术的革命。任何解释都必须考虑社会、政治语境以及波洛克作品主题的相关性,特别是因为其声称具有个人经验的普适性。这里的推测必须以波洛克的主题为中心,因为它从写实的“美国风景”、30和40年代象征的和叙事的形象,转变为成熟时期的主观和抽象的作品,并具有普适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经验的真实写照。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源于当时美国的特殊情况,包括大萧条的社会政治经验,以及与欧洲和二次世界大战现场的隔绝。〔28〕
虽然我拒绝艺术自动地“反映”社会的看法,这些是我希望在接下来的部分回答的问题。只有当我们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们才能开始理解为什么到了1948年人们不再能够说,就像人们之前开玩笑时所说的那样,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从野蛮到衰落而中间不经过文明化过程的国家。〔29〕[原著为法文,本文依据此书英文译本“引言”部分译出:Serge Guilbaut, 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Abstract Expressionism, Freedom, and the Cold War,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rthur Goldhammer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introduction, pp. 1-18]
注释:
〔1〕这从1982年巴黎蓬皮杜中心举办的波洛克展览画册的前言中就可以看出来。在前言中该馆馆长多米尼克·波佐重复了格林伯格的陈词滥调,即这个美国艺术家顺理成章地从形式上跟随毕加索、马蒂斯及蒙德里安。这个美国艺术家加入了万神庙的众神之列,而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只有为他烧香:“波洛克是宇宙创造进程中最伟大的里程碑或中途站之一。对于这一级别的人物,身份的概念变得毫无意义。”虽然这本画册是一个传记信息的金矿,它小心地避免了检验这个画家的作品与美国历史的关系。其中的评论文章均是作家或诗人的著作,他们使自己局限于印象式的或形式主义艺术史家的解释。
〔2〕要确信这个断言的真实性,只需注意美国媒体对呈现于1913年军火库展览以及在阿尔佛莱德·斯蒂格利兹的“291”画廊展出的现代艺术的强烈反应就够了。不要忘了抽象表现主义代表着美国人首个创造一个围绕着一群具有共同思想并决心取得国际声誉的艺术家和评论家有组织的前卫的尝试。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斯蒂格利兹与他的艺术家当然确实为现代艺术辩护,但是他们从未梦想过取代巴黎。对国际联盟的不满加上美国战争努力无效的感觉,导致了整体的紧缩以及民族主义的增长,后者很难说对前卫的诞生有利。当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的迹象在地平线上隐约显现时,这种民族主义转化为国际主义。与此前的战争不同,这场战争释放出一个好斗的美国国际主义,其中现代艺术扮演了一个主角。
〔3〕例如,杰克逊·波洛克在纽约与墨西哥壁画家西盖罗斯合作。他从事着宣传性壁画的实验。有一张照片显示波洛克于20世纪30年代在一辆五一劳动节的彩车前留影。马克·罗斯科曾画过都市风景和地铁等现实主义的场景。佛朗兹·克莱因、菲利普·古斯顿和布莱德利·汤姆林直到1948年后才转向抽象。
〔4〕Harry S. Truman, “To the Congress on the Threat to the Freedom of Europe”(就对欧洲自由的威胁在国会的讲话),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4).
〔5〕Harry S. Truman, Off the Record: The Private Papers of Harry S. Truman(非官方文件:杜鲁门的私人文件), edited by Robert H. Ferrell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0), p. 129.
〔6〕Pierre Cabanne, “Pourquoi Paris n’est plus le fer de lance de l’art”(为什么巴黎不再是艺术的先锋), Arts et Loisirs 87 (1967): 9.
〔7〕贝吉奥兹、戈特利布、纽曼、罗斯科和斯蒂尔未包括在这次展览中。
〔8〕See Serge Guilbaut, “Création et développement d’une avant-garde: New York, 1946-1951”(前卫的诞生与发展:纽约1946-1951年), Histoire et Critique des Arts, July 1978, pp. 29-48.
〔9〕Irving Sandler, The Triumph of American Painting(美国绘画的胜利)(New York: Praeger, 1970), p. 1.
〔10〕Georges Duby and Guy Lardreau, Dialogue(对话), Paris: Flammarion, 1980), pp. 101-2.
〔11〕See Carol Duncan and Alan Wallach, “MOMA: Ordeal and Trimph on 53rd Street”(现代艺术博物馆:53街的折磨与胜利), Studio International 194, no.1 (1978): 48-57.
〔12〕桑德勒在另一本书里对1950年代有类似的处理,The New York School(纽约画派), (New York: Praeger, 1978).
〔13〕Kurt W. Forster,“Critical History of Art, or Transfiguration of Values?”(艺术的批判性历史,或价值的转化), New Literary History 3, no. 3 (1972): 467.
〔14〕Dore Ashton, The New York School: A Cultural Reckoning(纽约画派:一场文化的清算), (New York: Viking, 1973); David and Cecile Shapiro,“Abstract Expressionism: The Politics of Apolitical Painting”(抽象表现主义:非政治绘画的政治), Prospects 3 (1976): 175-214; Jean Laude, “Problemes de la peinture en Europe et aux Etats-Unis, 1944-51”
(欧洲与美国绘画的问题,1944-1955年),in Art et ideologies: l’art en occident 1945-49 (St. Etienne: CIEREC,1978), pp. 9-69. 值得一提的还有John Tagg, “American Power and American Painting:The Development of Vanguard Pain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45”(美国实力与美国绘画:1945年以来美国前卫绘画的发展), Praxis 1, no. 2 (1976): 59-79. 尽管对传统历史持批评态度,这篇文章所持观点由于太接近阴谋论而没有什么用处。
〔15〕Jane de Hart Mathews,“Art and Politics in Cold War America”(冷战时期美国的艺术与政治),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1 (1976): 762-87.
〔16〕马斯林·普雷奈特写了许多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特别是 “Pour une politique culturelle préliminaire,” in Art et idéologies, pp. 89-102.
〔17〕Robert Carleton Hobbs and Gail Levine,“Abstract Expressionism: The Formative Years”(抽象表现主义:形成时期), (New York: 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 1978).
〔18〕当这个偶像化的研究得到改善时,只有一处改变(出于自责、时髦以及高贵的义务的综合原因):将莉·科拉思纳包括进来。
〔19〕有关这个话题有意思的讨论见于Russell Jacoby, Social Amnesia: A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from Adler to Laing(社会性失忆:当代心理学批判),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20〕与此有关的使人想起迈尔·舍皮偌(Meyer Schapiro)态度上的变化,在这一时期他成为另一位“非政治”前卫的推进者。
〔21〕Eva Cockroft,“Abastract Expressionism: Weapon of the Colad War”, Artforum 12 (June 1974): 39-41, especially p. 39.
〔22〕许多未发表艺术家的文字保留在华盛顿首府的美国艺术档案馆。
〔23〕Letters from Andreas Feininger to Mark Rothko, October 12, 1949.
〔24〕Hilton Kramer,“Muddled Marxism Replaces Criticism at Artforum”(在《艺术论坛》杂志,混乱的马克思主义取代了批评),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 1976, section 2, pp. 1, 16.
〔25〕“革命的年代”是一个自1974年11月至1975年9月在法国和美国巡回展出的一个小规模展览。这些文章由重要的国际权威签名:Pierre Rosenberg, Frederick J. Cummings, Antoine Schnapper, Robert Rosenblum.
〔26〕Carol Duncan,“Neutralizing the Age of Revolution”, Artforum, December 1975, p. 50. 罗森布朗的回应出现在Artforum, March 1976, p. 8.
〔27〕Kramer, “Muddled Marxism,” p. 40.
〔28〕Bernice Rose, Jackson Pollock: Drawing into Painting(杰克逊·波洛克:卷入绘画),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80), p. 23.
〔29〕引用于USA:The Permanet Revolution(美国:永远的革命),(New York: Prentice-Hall, 1951), p. 221.
秦兆凯 旅美学者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1年第3期)
本文来自季末投稿,不代表胡巴网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hu85.com/172861.html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xxxxx@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